|
拉卡拉POS机 http://www.hejifuwu.net 1935年的秋天,在巴黎留学的常书鸿来到塞纳河边的小书摊,无意中翻到了一套《敦煌石窟图录》,收录了汉学家伯希和在中国敦煌莫高窟拍摄的壁画、雕塑作品300多幅——常书鸿从未见过这么精彩的中国画作。 已在巴黎画坛崭露头角的常书鸿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放弃巴黎,回国去敦煌。“我决心离开巴黎,而等待着我离开巴黎的是蕴藏着千数百年前民族艺术的宝库的敦煌。”他说。从塞纳河畔到北平街头,从山城重庆到河西走廊,常书鸿辗转8年,跨越千山万水,终于走到了魂牵梦绕的敦煌。 “到西部去!”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到40年代,一批批艺术家怀着这样的理想,坚定地踏上西行之路。艺术家们经历了动荡时代下文化格局的分流与聚合,内心经受着震动并完成向现实的艰难转型。一代中国美术家将古来通向西部的刑罚之路、流放之路、冒险之路,踏成一条面壁投荒之路,一条艰难而又充满奇遇的探索发现之路,一条中国艺术家的成长之路。 “作品既富,而作风亦变,光彩焕发,益游行自在,所谓中国文艺复兴者,将于是乎征之夫。”徐悲鸿当年曾这样评述吴作人的西部之旅,而这又何尝不是那一代艺术家的艺术经历与成果。而今,这种从中国传统艺术中寻找滋养的“传统”,也在几代艺术家的身上得以展现——他们通过写生或临摹,都从中国传统艺术中认识到具有东方和本土特征的造型体系,特别是从创作上“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敦煌石窟艺术实证了中国美术发展的历史,克孜尔石窟壁画令现代人惊叹不已,中国的传统艺术土壤,成为一条传承之线,为当代中国美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而中国当代美术繁荣昌盛的历史根源和强盛底气,也正在于此。 康春慧,《云林集·之十一》,69x92cm,设色纸本,2022 靳尚谊:文化精神之旅 “丝路明珠”敦煌石窟艺术,见证了东西方多元文化汇聚融合,更如一块磁石,吸引一代代的中国美术家亲身前往,临摹、写生、创作,汲取敦煌艺术中民族文化的精神给养,书写他们每一个人与敦煌的故事。 油画家靳尚谊的“敦煌故事”,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开始了。1978年,他在常书鸿的带领下远赴敦煌,住在当地的一个小招待所里,“那个时候敦煌的游客不多,前来参观的人很少,所有洞窟都开放给我们临摹,没有限制,因此我们参观得非常细致。”靳尚谊回忆。 他们在敦煌待了半个月,靳尚谊没有沿袭张大千开创的以线描为主体的传统壁画临摹方式,也与其他人用水粉临摹的方式不同,他每天用油画临摹洞窟壁画,“而且都是临局部,挑选我喜欢的部分临摹,用写实的方式把敦煌那些已经氧化破损、以及墙上斑斑驳驳的景象全都描绘出来”;他认为,这种视觉效果用油画画起来很有意思,“它就像是油画中的灰调子,复杂而和谐”,“比如人物的皮肤以前是白色的,后来变成黑的,变化之后就很复杂了,油画这种艺术语言恰恰是最能直接反映出当时看到的敦煌壁画的景象的”。“我做过很多展览了,这个展览的方式很特别,很有意思。”靳尚谊所说的,就是8月19日至10月23日在南池子美术馆举办的沉浸式展览“我与敦煌——靳尚谊、唐勇力绘画展”:公众步入美术馆,看到靳尚谊笔下的“美人菩萨”与唐勇力笔下的“虔诚藏女”构成的整幅海报,就能感受到敦煌艺术之光,引领大家进入千里外的敦煌大漠。 南池子美术馆“我与敦煌——靳尚谊唐勇力绘画展”现场 走进展厅,千年岁月的历史记忆与敦煌洞窟的壮观面貌通过沉浸式的展厅设计表现出来,幽暗的展厅配以明亮的灯光,营造出洞窟的神秘氛围。展览入口的天顶上仿照敦煌覆斗顶殿堂窟布置了纹样精致的藻井,为展览开篇添了“敦煌色彩”。一层展厅搭建出靳尚谊进入敦煌石窟内创作写生作品的场景,同时展出了靳尚谊当年在敦煌写生的6幅作品:北魏第254窟南壁上的《萨埵太子舍身饲虎》、隋代第404窟西壁龛内北侧的《供养菩萨》、初唐第57窟南壁的《观音菩萨》和西壁龛内南侧的《供养菩萨》、第220窟北壁大幅《药师经变图》局部里的《供养菩萨》、元代第3窟北壁《千手千眼观音》的局部人物“老年男性婆娑仙”,带领公众完成一次穿越不同艺术媒介、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继承与创新的敦煌文化精神之旅。 1979年,靳尚谊又到山西永乐宫考察,中国古代壁画艺术中优美的造型、流畅而富有弹性的线条、年久变色而更具典雅辉煌的色彩使他激动不已。在这一阶段,靳尚谊作为中国艺术考察团成员,亦曾到西德考察美术教育,考察波恩、西柏林、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等地的艺术博物馆,第一次看到丢勒、提香等欧洲古典大师的作品,特别是波提切利流畅有力的线条、明朗辉煌的色彩、富有平面趣味的装饰,引起他浓厚的兴趣;1981年底,靳尚谊赴美探亲期间,系统考察了从古埃及、古希腊直到美国当代的艺术。不断向西方油画传统学习,同时不断向中国文化传统掘进——靳尚谊一直“两条腿走路”。 靳尚谊《临莫高窟第〇〇三窟(元代)婆娑仙像》53.4x39.7cm纸板油画1978年 他逐渐意识到,不能再重复大师们的老路,必须在吸收西方绘画营养的同时,立足于中国传统的土地,使西方油画和中国传统艺术融会贯通。“临摹敦煌壁画,我的收获很大,在我后来的创作风格里,吸收了不少东西。比如我根据壁画的形式画了一批肖像,《画家黄永玉》《归侨》《探索》就是分别用黄永玉的画、永乐宫壁画做背景,将壁画的传统内容和油画结合起来。”靳尚谊说。 “敦煌写生,既是研究中国传统艺术的重要方式,也对我后期的油画发展有很大影响。”在一系列壁画寻访与西方考察后,靳尚谊结合中国传统壁画样式创作出一批具有平面装饰效果的经典作品,影响深远,他的创作面貌为之一变——《探索》《思》《画家黄永玉》《夏季牧场》等一系列作品,逐步地、多方面地吸取了中国传统壁画艺术的特点。而这一阶段,也是靳尚谊探索中国传统艺术和欧洲传统艺术的交混期,他着力于探寻如何用油画语言展现中国传统,并开创了具有鲜明个人标识性的中国化的油画语言方式。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油画面临着新旧观念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处于“全盘西化”或是“油画民族化”的十字路口。1983年的中央美院油画系教师作品展上,展出了一幅名为《塔吉克新娘》的油画作品。画中的姑娘形象优美、宁静,表情略带羞涩、拘谨,给观者以纯洁的触动;新娘身披红色方形大头巾,沐浴在来自画面右侧的强光之中,面部轮廓清晰,色彩和明暗关系非常响亮、厚重。这幅画成为靳尚谊艺术生涯中最负盛名的杰作,也成为中国油画新古典主义语言风格的扛鼎之作。这一时期,靳尚谊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场景单纯、画面柔和、刻画细致、表现含蓄、情感丰富。在这样的积淀中,靳尚谊孜孜以求的古典主义绘画语言风格趋于成熟。 靳尚谊《临莫高窟第五十七窟(初唐)观音菩萨像》55.2x39.4cm纸板油画1978年 上世纪90年代的《晚年黄宾虹》、新世纪以来的《八大山人》等作品,逐步使他形成了自己的油画民族化之路;进入新世纪之后,他对于画面单纯的形式追求和纯化语言探索,更使佳作迭出—《瞿秋白》《窗下》《果实》等一系列深受欢迎的精彩作品和许多人体系列作品相继完成,实现了他在艺术上的飞跃。 《画家黄宾虹》《晚年黄宾虹》《髡残》《八大山人》等诸多作品都展现出了中国意韵与风格——宾虹先生的墨韵、髡残上人的禅味、八大山人的冷逸;作品更近似于古典主义、印象主义和现代主义三种语言风格的折中,逐渐成就了靳尚谊艺术的高峰。“就我个人而言,油画创作中也会不断注入中国文化的内涵,从东方壁画、水墨画里吸收营养。我认为,具有东方文化内涵的油画会出现,但不要刻意追求,要自然而然地形成。”他说。对他而言,沉浸融贯中西的油画艺术逾七十载,最大的收获就是中国人也能熟练地掌握西方油画的技法:“在表达自己的追求时,兼顾中国的文化内涵与西方油画的精湛技巧,使自己的作品呈现一种不同于西方状态的新的抽象美——我想为这个目的,付出毕生的努力也是值得的”。 唐勇力:再创唐风之梦 对靳尚谊而言,敦煌是风格与技法转折的“触发器”,而对国画家唐勇力而言,“敦煌之梦”系列成为了他的代表作——在“我与敦煌”展览总策划宁强看来,唐勇力“对敦煌壁画的研究、借鉴更加直接、更加明显,既赋予了敦煌壁画以当代性,也给当代中国工笔画注入了传统艺术血脉之力”。 踏上“我与敦煌”二层展厅,眼前出现的是“白雁西风紫塞,皂雕落日黄沙”的大漠景象;作品前均铺设仿古莲花砖,以莲花纹为中心,周围环饰蔓枝纹,砖面纹饰为模制阳文。高度还原的砖石质感、精致纹样,与灰色系的纱幔石窟布置呼应。在其中,观众可以欣赏唐勇力“敦煌之梦”系列中的20件作品,同时感受画家本人上取汉唐古法、直绘现实人生,在斑驳古韵中融入自己的探索与创新,匠心独具、不落窠臼的艺术水准。 1980年,当学生时期的唐勇力第一次走近敦煌壁画时,他不仅惊叹于千年前创作佛教壁画的画工们精湛的技艺,更加坚定了一种信念:伟大作品的核心力量来自于艺术家虔诚的心。“置身于莫高窟,窟内丰富而璀璨的壁画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这些作品不仅规模恢弘、技艺精湛、历史悠久,凝聚着中原与西域文化在交融碰撞中的融合与积淀,还因长时间的岁月变迁、风侵水渗,呈现出斑驳陆离、晦明变化的艺术效果,无疑是在古代壁画原貌上借助大自然的再创造达到了极限的美感。”他说。 唐勇力《敦煌之梦——悠悠岁月》84x80cm绢本设色1996年 “我在感叹,画工们用一种虔诚的心态创作出了千古流芳的绘画艺术作品,从敦煌回来以后,我也立下了这样的志向:要像虔诚的佛教徒一样去对待艺术,画出高水平、高质量的作品来。”之后数年间,他多次到访敦煌,深入研究不同时期的壁画,尝试在创作中借鉴、挪用、再现敦煌壁画的元素,最终探索出“虚染法”与“脱落法”——运用虚染法,营造水与墨相互渗透、彼此交融的悠长意韵;运用脱落法,营造岁月苍茫、静穆沉雄的历史厚重感——两相结合,创作出“敦煌之梦”系列作品,用现代人的眼光重审、继承和发扬敦煌艺术精神。 中国画向来注重文人画精神,但唐勇力在艺术创作实践中一反文人画传统,而以汉唐绘画即画工画传统为师法的基点;传统的工笔人物画只在轮廓线的内部平涂、渲染,但唐勇力却多采取“内外皆染”的方法,轮廓线在许多地方被淹没在一片墨氤氲之中,造就了一片朦胧之境。虚染法的创造与使用,使得工笔画变得苍润厚重,更加具有写意性,因而他的画取法了唐人的博大精深和宽阔胸襟以及创造力,又显示了中国传统的正大气象,焕发出了无限生机和神采。 “二三十年来,他多次到敦煌考察,但是并不是简单地学习、临摹敦煌壁画,而是注意壁画在历史的流程中经过岁月的剥蚀,出现的那种颜色脱落的痕迹,他把这种痕迹拿到自己的绘画中,使之变成自己的一种技法、一种肌理——事实上,肌理这个概念与西方引入的现代艺术手法语言有关。”评论家薛永年曾这样评论唐勇力所探索的“脱落法”。 唐勇力《敦煌之梦——绿色希望》155X136.5cm绢本设色2001年 古代青铜器的表面产生的铜锈,有色彩斑斓的肌理效果;古代壁画因自然风化,久经风蚀,有变色或者部分剥落的现象。岁月无声却充满无限力量,它在万物上留下难以掩藏的印记,就如同树木的年轮般无法掩盖,同时又具有难以言说的魅力。多年来唐勇力所探索的“脱落法”恰恰就是追随在古代壁画和古青铜器表面由岁月留下的沧桑感—他将敦煌壁画的自然剥落作为表现效果,进而在绘画创作中表现客观形象。 “脱落法”在材料的选择上很讲究,首先需要伸缩性很强且不易破损的纸或绢,用矿物颜料勾线和染色完成以后,他要根据画面的实际需要,用与胶调和好的蛤粉在部分位置进行厚涂,待画面完全干后,或让蛤粉自然脱落,或用打磨、水洗等方法进一步调整。在《敦煌之梦——绿色希望》《敦煌之梦——大唐盛世》《敦煌之梦——祈祷太平》等作品中,他在完成勾线和层层敷色等程序后,在深色的底子上,使用蛤粉在画面中长者的衣服上做了大面积的厚涂处理,在壁画人物的皮肤上也涂了少量蛤粉;待干后打磨,进而产生部分脱落的艺术效果,使画面呈现出一种古朴且沧桑的艺术特征,让作品弥漫“静谧感”。 《敦煌之梦——千手观音》《敦煌之梦——西部石匠》《敦煌之梦——与佛有缘》等诸多作品中,唐勇力都将佛教文化、历史传说与现代人的生活日常联系起来,希求打破时空界限,将历史与时间、传统与现代、传统佛教信仰与当代民间佛教信仰之间千年相续的联系融合在一起。特别是《千手观音》,画面中心的小女孩被视为佛的化身,艺术家再次以敦煌式的构图、斑驳的色彩表现古时今日对纯净圣洁及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物象时空的并置和多重激发的叠加所营造的“敦煌之梦”中,唐勇力以精湛的艺术技艺“再现”了敦煌壁画的现状:土质墙体上的绘画已经剥落,颜料在氧化、盐碱化的作用下自然变化;人物以红褐色、赭石色勾染轮廓和肤色,白色矿物质颜料以“脱落法”绘制出衣袍和头发;尤其是不均匀的染色,营造出空间的模糊感,都构置一个富丽雄奇的“梦境”。 唐勇力《敦煌之梦——西部农人》79.5×84cm绢本设色1996年 在“梦境”中,这些斑斑驳驳的肌理样式,形成一种视觉上的“时间感”,在精神气质上追求更为深宏博大之美。“肌理作为一种‘自然语言’,我们可以在运用中驾驭它、强化它,使之变成个性语言……发挥肌理的特性并与其他语言有机结合,使之相互协调,同时并存,会丰富中国画这一特定画种的语言。”他认为,“做肌理”可以不限于画面的一个局部或一隅一角,而他通常的做法是从图像到图底统统做足,呈现一派“满堂彩”的图式。 这样的图式创造出来的观感与审美意象,是唐勇力在不断赴敦煌考察和体验而来的,是一种悠远的历史感——一种厚重、饱满、古朴的谦和美,不断涌动在唐勇力的画面之上。再创敦煌唐风之梦,唐勇力在创作中,更关注的是个体的内在精神体验,而并非仅仅“现实主义”的艺术观念,因此,他的这种创作方式俨然成为一种“修行”,“敦煌之梦”也就成为创作者的“心象”。 康春慧:纵贯时间长河 艺术家康春慧的《云林集》系列组画,融合了柔软易逝的桃花和坚硬恒久的太湖石;被无数艺术家描述和描绘过的《丽达与天鹅》,在她的笔下,画中两个物种既像纠缠又似对抗;将影像与水墨融合的作品《物云云•峙》,光影之间,挪用神话故事的画面拉长历史的时间线,更成为她在代语境中重新梳理水墨艺术的创作理路的代表性作品。 它们当然不是康春慧将多重意味的文化元素相互叠加的“新尝试”——甚至,她的创作之路,就是多元文化叠加的过程——来自乌鲁木齐的她定居北京,正在以东西方神话故事为文本,用水墨方式重新建构一种沟通多种文明的艺术面貌。在这条创作道路上,来自新疆特别是克孜尔石窟的艺术滋养“时隐时现”。 《物云云·峙》190x220cm设色纸本及影像2016-2017 5岁跟随父亲学画画,少年时代经历过近乎苛刻的训练后,2000年,刚满18岁的她便决计从故土、从水墨中出走,去品味更多目光之外的世界。“我故意选择了非绘画的专业”—她从遥远的新疆来到陌生的江南,投身于公共艺术专业;本科毕业,她突然“转场”,进入韩国首尔大学学习新媒体艺术。 看似她的求学与求艺之路,会离故土文化越来越远。然而,她又“转场”了——2011年,康春慧在首尔大学递交了自己的研究生论文,一份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研究。24岁那年,在敦煌与克孜尔的抉择中,她选择了离故土更近的一方:在距乌鲁木齐800多公里处,丝绸之路的首站古龟兹,有着西域地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洞窟类型最齐备的佛教石窟寺遗存——克孜尔石窟——她在那里研究了一年。“它带给我最深的印象其实是那种大体量的包覆感,压抑且震撼—部分石窟坍塌后中央空荡荡的佛龛,我经常会站在前面默默看很久,想象着那里曾经有一尊佛像微笑着用不好捕捉的悲悯眼神看着我,看穿我无法改变的一切,令我平静而沮丧。”她回忆。 克孜尔石窟以笔法精妙、色彩富丽见长,自成一套视觉逻辑。当她临摹壁画,在为斑驳残存的历史所震撼的同时,在立体感极强的凹凸晕染技法里,她也寻找到了与水墨的契合点。于是,“沿着壁画脉络,探索当代水墨的艺术道路”成了她往后的心之所向:“我从斑驳的历史中,看到了非常好奇的东西。” 2014年,当康春慧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个水墨系列作品时,就选用了八九种矿物颜料,颜色厚重;凑近仔细看,作品又像是经历了岁月的痕迹。她吸收了克孜尔壁画的特点,以青金石、孔雀石、绿松石、红岩泥等矿物作为原料,自己研磨、制作,调完胶后,她会控制颜料研磨的粗细,大多保留较大颗粒,以此来制造涂色时颜料滞留带来的肌理感;这些色彩充满温润的厚重感,让作品画面具备了时间的力量。“比如青金石、朱砂,具有极强稳定性,就能长时间保持原色不褪。但也有例外的矿物颜料,像雄黄和雌黄,就会受到氧化和光照的影响。”她喜欢画面上均匀或不均匀的感觉,也会故意制造色彩层层覆盖的基底感,这是矿物颜料赋予她作品的魅力。 她曾认为壁画不好掌握、宗教和艺术之间的关系难以拿捏,一旦钻研就容易被体制框住,而使创作过于“壁画感”。而经过了多年的消化与理解,康春慧终于谨慎地将壁画的东西提取、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上。 《丽达与天鹅》,315x188cm,设色纸本,2019 康春慧近些年的代表性作品、三联屏水墨组画《隐逸的主角》,创作灵感就来自于克孜尔石窟的中心柱窟。它有着半弧形拱顶,仿佛从一座建筑上剥落下来,“能空降”在展览现场。在用色上,康春慧吸收了克孜尔石窟的色彩逻辑,厚重沉稳中不失美艳,而天然矿物颜料的使用,更让人感受到某种经历了淬炼却历久弥新的时间分量。 克孜尔艺术牵引着她,兜兜转转回到水墨,又兜兜转转回到了花鸟——从2015年,康春慧的首个个人画展以“执花寄月”为主题,一月兰、二月梅、三月桃、四月牡丹……用十二花神代表一年十二个月份的更迭,“这些花千百年没有变化,但在不同的时空中又有着不同的意义—花卉以最为平实的存在诉说着崇高而又神秘的自然感”。2017年,她创作出另一个名为“物云云”的新系列作品,取“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而不知;浑浑沌沌,终身不离”之意——世间万物最终都会回到其根源。“从‘执花寄月’系列到‘物云云’系列,我像是从描写永恒时空到描写永恒时空中生命能量转换的时刻。”她说,“物云云”系列的色彩主要就源于克孜尔壁画:“古人在绘制壁画时可用的颜色很多,但最终选择的色彩主要只有几种,使很多壁画呈现出的颜色一目了然。” 在这样的创作中,康春慧完成了从真实到再造的转变,不变的是对“根”的描绘:“执花寄月”的每幅画都是从画根开始的:“下半部分的造型是传统器皿的器型,但全都是根蔓缠绕而成的;上半部分,则是中国传统的折枝。”“物云云”系列中的“根”,不仅是植物之根,也是万物之根,更包含生命、连结、维系等多重意味。起初,被根包裹的物像还能看到眼睛或肢体,但随着系列的深入,她画面中根的缠绕力度越来越大,这些物像也被遮挡得更加抽象了起来——在一切时空中传递着能量。 《PhantasiaⅠ》,91x91cm,设色纸本,2019 近年来的创作里,康春慧对于根系的表达又走向了一个新的向度:那些被缠绕的物体如同被历史与文化所关联,彼此之间缔结了更多重的情感,传递着更复杂的信息,一如“执花寄月”展览策展人吴洪亮评价的那般,是在“续接断裂的传统,在寻根中寻找力量”。 对她而言,克孜尔艺术也是“根”。最近几年,康春慧的创作多以神话故事为母题,除了以希腊神话和北欧萨加为主的“Phantasia”系列,还有中国神话“山海经”系列,这些新作又展示出她思想维度的体量——她试图在东西方文明之间思考、融汇,探索文化误读的边界,将水墨引向了崭新的开阔地。 从中国传统艺术的故土中,康春慧一路走来,正如那生长着的根系,末梢从四方大地迂回着汲取养分,最终又会回归到扎实而永恒的中轴之上——康春慧说,她一直不太喜欢把自己的性格完全暴露在创作中,她宁愿随着时间一点一点地往向外展开:“我的作品不想给谁教导,也不希望仅是装饰,更像是我思索的阶段性总结,是给下一段深思提供的材料。而这种思考会一直进行,等待着每一张作品结束后瞬间的寂静。”但每一次、每个系列开始的时候,自己内心都会有明确的感受—这次好像又脱了一件“衣服”——对她而言,一幅画,从题材选择,到笔墨试探,都可以纵贯时间长河。 编辑/马雪莲 文/德加 新媒体编辑/欣仔 新媒体设计/ChanningZ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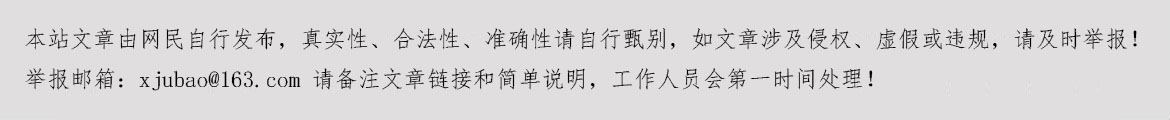
|